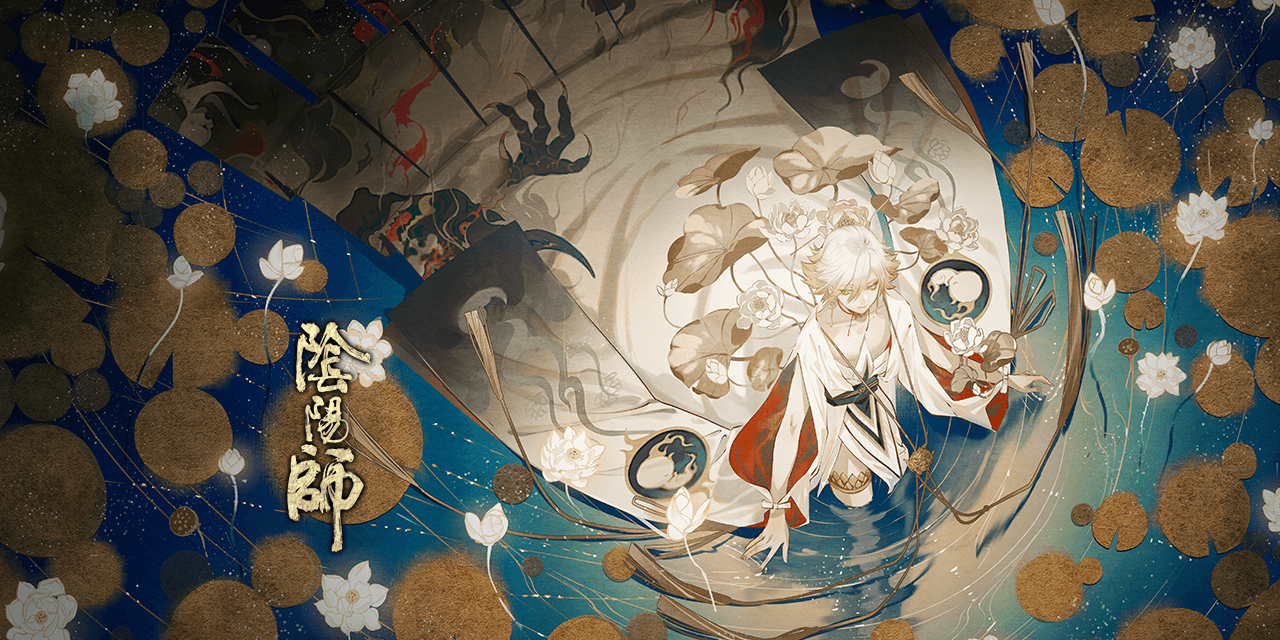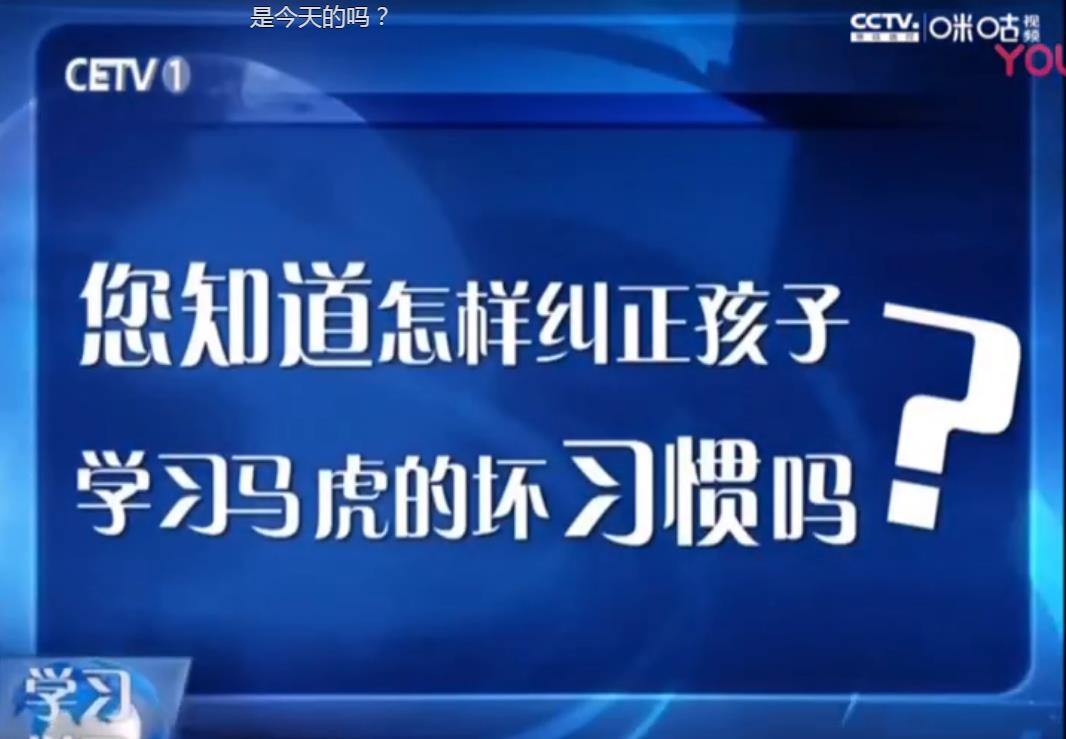cf保存截图 从古音到现代方言,让人“捉摸不透”
本文约3800字
阅读需要10分钟
所谓发音不同,十里不同。 在普通话日益普及的当下,各种方言依然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的“硬通货”。 方言中还有各种新奇的词语,比如厬(fàn)旦、尰HU、妗子……如果你不是本地人,可能听不懂。
但回溯一千多年前,这些话并不新鲜。
是的,许多存在于现代方言中的“难以捉摸”的单词是我们的祖先最熟悉的。 不信的话就过来看看吧。
嫂子?从古代发音到现代方言
顾炎武曾在《唐云正》中提到过一个关于方言的有趣故事。
在青州等地区,有张家庄、李家庄等地名,但在当地人的口中,却叫张古庄、李古庄。 这不能归咎于当地朋友的发音不完美。 相反,这背后是有原因的。
如今,山东有各种各样的“村庄”。图源/高德地图
原来,在古代,“家”的读音是“古”。 《离骚》中有云:“羿游荡荒淫,善射夫封狐,狂傲以致新鲜尽,贪夫而丧夫”。家庭。” 顺着古人的押韵习惯,我们还可以发现,这里的“家”确实读作“gu”。 为此,顾炎武还在后面的文章中开玩笑说,后人觉得“城古村”莫名其妙,就改成了“城阁村”。 这真是一个笑话。
另外,青海等地方方言中“咕”的保留也是靠着这个缘分。 比如,东汉史学家班固的妹妹班昭就嫁给了曹师叔。 由于她才华出众,大家都尊称她为“曹佳”,“佳佳”从此成为对老年妇女的尊称。 这个称谓一直延续到后世,并逐渐融入生活。 即使到了现代,丈夫的姐妹也与“家人”联系在一起,成为“大嫂”、“嫂子”。
《妇女史图》中的班昭。资料来源/故宫博物院
远不止那些用古音输入方言的人。
北方地区常见的方言“妗子”常指阿姨,看起来完全没有关系。 但《集韵》中,姨字的辅音是“妗”。
有时候,古乐即使走了弯路,也能顺利穿越时空。 比如山东话里,屁股一般都叫“党”,这是有原因的。 “臀”本是形声字,古读音“甸”。 虽然后来逐渐演变成“蚚”,但也算是保留了前世的模样。 在河南的一些地区,人们常说的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也让很多外国友人感到困惑。 事实上,在几千年前,这并不算什么大事。 《说文·女部》解释得很清楚——“欢,齐君也生子。读若凡。” 《尊耀》说得更清楚,“齐人称生子为桓”。 正因为如此,最普通的母鸡下的蛋,发出古老的声音,变成了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“鸡蛋”。 又如,关西地区的人们喜欢说“物尽其用”,因为“废”的古音与“黄”相近。 久而久之,废墟的东西也可以“废墟”。
虽然品种繁多,但只能算是古语音与方言相遇的“碎片”。 放眼茫茫现代方言海洋,坚守古音的并不在少数。
独特的客家话光是发音就引人注目。 更何况,从发音特点来看,客家话就像是历史的宠儿。 古代人们的发音与现代有很大不同。 其中之一是“汝声”的保留。 不幸的是,随着语言的发展,汝声逐渐“消失”,并融入其他声调中。 这就是所谓的“入派三声”。 正因如此,在大多数现代方言中,人们已经找不到语调的影子了。 客家话是为数不多的“幸存者”之一,保留了大量古代入声的韵韵和词尾。 江西的赣语也或多或少地抓住了入声的尾音,让这个“难以理解”的名字成为了大家的“熟悉的陌生人”。
客家传统民居。来源/纪录片《追寻客家民俗》截图
如此看来,“相隔十里,音不同”的事实也并非一成不变。 毕竟,运气好的话,古今之人可以互相交谈。
好看吗?从古书到日常用语
对于方言来说,中华文化博大精深,仅仅借用一些单词的读音岂不可惜?
为了继承古老的语言,方言们想出了办法。
比如,在山东的一些地区,凡是胡编乱造的人都会被形容为“蟟”(tāo)。 早在战国时期,这样的表达方式就不是什么新词汇了。 《荀子·恶性》曾用过,所谓:“其言也无礼,其行也矛盾,其行而悔,是小人之学也”。 又如,“木住”一词在当地人口中也写作“木强”,用来形容人木讷、反应迟钝。 其实,他们也有“前世故事”。 《汉书·周勃传》也用这个词来形容周勃的性格,形容他“坚强而诚实”。 《汉书·凉吏传》云:“官民日渐枯萎,气木强而文弱”。 这也是这个意思。
《荀子》书影。来源/中国国家图书馆
在古汉语、古汉字最集中的关西地区,这样的情况更为常见。 在干县,人们遇到漂亮的女人,多半会说“漂亮”。 有时候当你说某样东西很美的时候,你就会说“廖非常”! 这些不是当地人提出的赞美之词。 在《说文解字》中,廖、习都是“好貌”的意思。 还有《诗·大雅》中“太人怀孕,生文王”的说法,成为形容怀孕的雅称。 当女人怀孕的时候,她就变成了“怀孕”。 与此类似,青海话里有“序列”,其实就是嫂子的意思。 在《史记》或者《汉书》中,也有很多这样的表述。
山东淄博、沂蒙方言中的“谰(dòu)枕”一词,让人乍一看还以为是某种黑科技宝物。 经《说文解字》查,原来“谰”不仅是古人对脖子的称呼,也是古代齐地方言词。 从枕头到“谰枕”,瞬间就顺理成章了。
忆梦枕。 来源/沂蒙晚报2021.8
还有銊(ào),乍一看有点历史感。 《水浒传》里有“热锅上蚂蚁”的说法。 在河南话里,仍叫“豆子”。 这没什么不寻常的。 这是一个铁锅。 当地人喜欢吃煎饼或煎饼。 我所有的朋友都非常熟悉它。
有时候古书还不够,传说、民俗也可以凑热闹。 比如关西方言中的“妖婆”、“妖娘”就不是神。 传说舜的继母名叫尧。 这个后母不是好人,专门虐待舜。 她还“出名”、“臭”了数百年,以至于关西地区的人们常常称呼继母为“姚妈妈”、“姚妈妈”。 与古书、古书相比cf保存截图,传说、古俗相对奔放,与这些相关的方言更容易让人迷惑。
例如,“头谷”字面意思是第一个小米,或者至少它必须是一种植物的名称。 但真巧,它其实就是牛和马的意思。 原来,古时候,人们喜欢在山谷里放牛马,所以有“粮量牛马”之说,就是说谷子里有几头牛马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在一些地区的方言中,人们也将牛、马的名称改为“头谷”。
而“咕咚”,在很多人看来,不就是“古董”的误写吗? 众所周知,古代的物体一般都称为物,古物就是古物。 但在后来的表达中,人们习惯性地省略了“西”字。 这样看来,地方方言中的“古东”其实比“古东”更好。 “古董”比较正统、合理。
嘎(gǎ)也是其中之一。 古代的钱币较小,人们喜欢称其为“嘎”。到了现代,“嘎”虽然失去了“铜味”,但仍然没有摆脱“小”的含义。 例如,在甘肃,人们喜欢称呼自己的孩子为“嘎娃”。 有一天,巷子里飘出了饭菜的香味,家长们纷纷喊“嘎嘎”。 “嘎”字的华丽变换完全丧失了。 。
《山海》中的嘎瓦。来源/电视剧《山海》截图
如果你看看北方方言,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 色彩斑斓的古名字就像留在沙滩上的宝藏。 尽管它们被时间的洪流冲刷了数千年,但它们仍然扎根于现代语言的沙子里。
重合?从前世传到今生
时间的车轮往往是最无情的。 古往今来,庞大的王朝、豪华的宫殿、珍贵的宝藏都湮没在时间的云烟之中。 即使是古老的技艺能够保存至今也是非常罕见的。
在如此一场“改天改日”的大清洗中,为何最不起眼的方言却能如此接近古老的谚语呢?
从逻辑上讲,面对相对难以保存和传播的实物和艺术,语言是一个例外。 在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中,有一种语言的历史层次理论。 简单地说,语言不是无根的浮萍。 相反,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表达方式,往往是经过人们几代人的积累而获得的。 这样,人们的方言也是不同时代人们的日常用语滋养出来的甜美果实。
如同一丛繁花似锦的树木,那些看似不经意间“失落”的古老名字,或许就是曾经在树根深处涌动的清泉。
事实上,这种代代相传似乎一直在发生。 以特色鲜明的巴蜀方言为例。 在近代川渝地区的常用表达方式中,既可以看到落叶,也可以看到老枝。 例如《说文解字》记载:“叔称母为姐妹,女儿,声在此。” 由于种种原因,这种表达方式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封印之下,等等。 “散”是蜀人对“笔”的俗称。 但也有一些词超越了时空界限,将基因刻进了现代巴蜀方言。 《成都通览》记载,明清时期,成都地区出现了“湘阴”(廉价的意思)一词。 清代《蜀话》中也有“距地远曰蹲,曰蹲”的记载。 如今,在成都街头,人们总能听到“白菜多少钱一斤?我们来尝尝吧!”之类的说法。 “我东西掉了,请你下来帮我捡起来。”
有人说他们都是本地口音,但他们的外貌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。
也许,它们只是站在树枝上的叶子。 折射古今之光,透过它们,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汉语乃至文化这棵大树是如何生根、成长、蜕变、繁盛的。
参考:
张崇臣撰。 古代文化丛书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20。
许慎撰。 《说文解字》[M]. 天津: 天津古籍出版社, 1991
李文石 撰; 刘铁城主编. 登上黄河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9。
丁胜树. 丁胜书文集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20.04。
张翰编. 播音员、主持人汉字发音手册第二版[M]. 北京: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,2018
现代成都话是怎样形成的? 成都方智公众号,链接:
结尾
作者 | 念苏
编辑| 詹千惠
校对| 火炬
*本文为《国家人文历史》独家稿件。 欢迎读者转发给自己的朋友。
国家日历好东西
“国家人文历史”公众号精彩集锦
一本了解中国古代传承与变革的书
《中国的历史我看不够》
有材料、戏剧和视觉
点击下图即可购买
↓↓↓
足不出户读书
国家人文历史杂志
点击下面的图片或
长按下图识别二维码
将个人历史导师装进口袋
“看着”永远是18岁~
阴阳师4月22日更新内容:帝释天上线技能调整,红莲华冕活动来袭[多图],阴阳师4月22日更新的内容有哪些?版本更新
2024-04-29四川电视台经济频道如何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与方法直播在哪看?直播视频回放地址[多图],2021四川电视台经济频
2024-04-29湖北电视台生活频道如何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直播回放在哪看?直播视频回放地址入口[多图],湖北电视台生活频道
2024-04-29